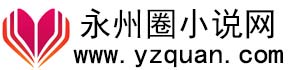30-40(18/37)
的幻痛,让他已经有几分恍惚了。但至少眼泪水是止住了,祁危自己都觉得狼狈,可他在齐棹跟前,就是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。
“……”
祁危动了动唇,好半天才从嗓子里挤出声音:“你刚刚,说什么?”
齐棹耐心道:“我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。”
祁危眼睫微动,大脑的刺痛和混沌感让他的眼皮不自觉地耷拉下去了一点,好像下一秒就要昏过去一样,幻痛好像还在持续,又似乎是小时候残留在神经的一点余韵,若有若无的:“不是…这一句。”
齐棹懂了。
“我说我不会怕你的。”
齐棹没有重复那个“好”,而是轻声跟祁危说:“再说我也没有必要怕你。”
没有必要怕他吗?
祁危不明白,为什么没有必要怕他。
他明明……
“你知道你多恶心吗”“你就是个怪物”“真是恶心的怪物”……
辱骂又从记忆里翻出来,祁危不受控制地轻颤了一下,痛苦地把身体蜷缩得更紧,好像恨不得自己现在是一只蜗牛,能够蜷缩着躲回自己的壳里。
可蜗牛那么脆弱,人类轻而易举地就能将他的壳粉碎。
齐棹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,但他上的课里有说过。
脱敏的过程就是在刺激中重塑新生。
所以他能做的只有利用这个时机去给祁危塑造新的观念。
“祁危。”
齐棹喊他,又告诉他:“我们认识这么久了,你都没有伤害过我,所以我没有必要怕你,不是吗?”
他想告诉祁危,如果不想被人害怕的话,就不要跟人动手,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
祁危就像是溺水的人,又被齐棹捞起来了一点。
他得以喘息,在混沌间应了声。
甚至在得知了不会被齐棹害怕的办法时,他还会拼了命地抓住。
“我不会……”
祁危用沙哑的嗓音呢喃:“我永远都不会…伤害你。”
他怎么舍得。
齐棹微微弯眼,没再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了,而是说:“地上凉,你能起来吗?”
祁危几乎是本能地点头:“嗯。”
于是祁危强撑着,带着很明显的轻颤慢慢从地上支棱了起来。
齐棹没有给他太多关注的眼神,从祁危的态度和话中,他更加确定了,祁危想要被当作正常人看,而不是一个疯子、精神病。
祁危重新坐回自己的齐人沙发上,柔软的感觉让他又稍微清醒了一点,尤其是他在看到齐棹去把被他折断了的铅笔和掉在地上的画板时。
祁危感到深深的懊恼。
他低下了头,像是做错事了的小孩一样,甚至开始无比痛恨自己:“……对不起。”
这话祁危都是咬着牙说出来的,不仅有几分切齿,还带着几分委屈。
他不是为自己感到委屈,而是因为自己控制不好情绪,感到难过。
齐棹稍顿,节俭的习惯让他下意识地把折断了的笔照样收进了笔盒,他微偏头,有几分奇怪:“为什么要跟我道歉?”
对他,祁危一直是有问必答:“我…吓到你了。”
齐棹实话实说:“是有一点点吧,但还好。”
他认真地看向祁危:“我更加担心你。”
祁危在他这两句话中,身体绷紧,又落下,但又还是绷了起来。
齐棹……担心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