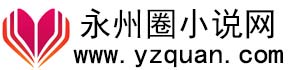60-70(22/26)
把自家大半底蕴都交到儿子手里,“我这就回太清峰将您常用的法器取来。而今,您先将这套定神钟拿去用。”说到这儿,邬九思从袖中去取出一枚锦囊,送到邬戎机面前。
他的表情已经不再是先前的平和,而是透着担忧。如今注视邬戎机,像是任何一个要眼看至亲踏入险境之人,不愿让对方离开,又知道对方必须前去。
如此氛围当中,旁边的修士们纵是心急,也说不出太多话来。人家几百年没见过面的亲生父子,好不容易重逢便是这样的场合,便是让他们多说两句话又能怎样?
再有——
目光落在邬少峰主手中锦囊上,也有人心头开始酸溜。别看在场众人身份上没什么区别,出了门也一样是让人尊重的“天一宗尊者”,可有些事,说不一样,便是不一样!
并非人人都有邬戎机当年的机缘,一个家中甚至不曾出过修士的小子,竟能从毫无仙踪的就山里走出来,一步步来到玄州,拜入宗门!
这还不算。在那以后,邬戎机的境界不断攀升。时至今日,放眼整个玄州、整个修真界,与他同样年岁的便只剩他的道侣——云州海上那头巨鲲倒是更长些,可还是老话,那巨鲲毕竟不是人修。
谁能不慕?又有多少人会因慕而妒?
上官冲视线撇开,压下心头哼声。
只是不等他回想起自己年幼时得父亲鞭策、又听父亲说起爷爷从前在邬峰主面前节节败退的场面,便听此人笑道:“九思,你且安稳些。我前面独自一人,都能在那歹人面前全身而退,何况当下?”
上官冲眉毛抖了抖,有些不解于这话。不过很快,邬戎机又用从从容容的声音告诉他答案。
“这分明是我与你娘特地托人为你炼的妙音钟啊!我记得一共是四十八枚?从前每日清晨,我们都要在你面前奏一首曲子。到了晚上,你就能直接将曲子复刻出来了。”
邬九思:“……”
邬九思“唔”了一声。
缓缓收回手,承认:“是我弄错了。这么看,定神钟应该也在太清峰上,我这便前去取来。”
他难得多了几分困惑。
与太初扇这样顶尖的法器不同,作为一套“玩具”,父亲、母亲设计这套妙音钟的时候是花了心思,可也仅仅如此。对于邬家三口人,这自是承载着珍贵回忆的物件。可对于外人来说,别说把其间细节打听清楚了,就连妙音钟本身,也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。
世上再有清楚父亲这些话的人,怕也只有一个郁青,一个当年的含元峰峰主了——后者兴许也只知道一半儿。至于郁青,则是因邬九思当日的告知。
自己其实想错了?眼前这个的确是父亲,他前面那些陌生之感,也不过是因为太久不曾与父亲相见?
至于为何对着诸多峰主、长老的争执冷眼旁观——将心比心,如果自己用心做事儿的时候还有一群人在吵来吵去的拖后腿,别说父亲了,就连邬九思自己也不是很愿意理会对方。
换个角度去想,前面让邬九思警惕的细节也变得寻常起来。他闭了闭眼睛,再睁开的时候,神色显然放松下来,对邬戎机说:“您再与那歹人相见,定要珍重自身!我还在等您,母亲也在等您。”
邬戎机笑了笑,再抬手拍拍儿子肩膀,这才转身离去。
至此,一场在旁人看来全无异常的父子对话便结束了。唯独袁仲林,从师侄身旁经过的时候又额外叮嘱了句:“九思,我知你也想与我等一同上阵,可你毕竟年轻,”一千二百岁,放在龙州、云州那些地方,也够当一个小宗门的太上长老,可这儿是天一宗啊,“就安心的将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