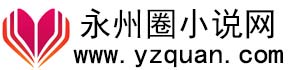190-200(27/38)
,手中匕首寒芒乍现,声音一字一顿,铿锵如泣血之音:“在杀死你之前,我要先杀死我的母亲千万遍——”朝徽帝陡然瞪大眼睛,苍白枯槁的肌肉开始颤抖。
“你说什么?”
那寒芒逼得愈发近了,只在咫尺之遥。
“这宫中日日唱着你的颂歌,却夜夜飘着你的叹息,”冰凉的刀刃沁凉,过了体肤连带起无穷的怖意,“我母亲那么年轻就死了,你心中没点交代么?”
朝徽帝辩解:“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?”
“别动,这刀子可不长眼,”卫云舟冷笑,“你看这玉坠好看吗?”
不知何时,卫云舟已经取下那枚玉坠,明珠周围是道道玉柱。
“这是囚笼,对不对?就像把她们深锁在宫闱之中的囚笼那样,”她难得靠这么近,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字都轰奏鸣响,“我害怕一旦我晚了一步,没能杀死母亲,就重新回到这囚笼之中。但好在你放松警惕,给我一个机会。”
她所说的机会,不过是他的恩赐——想要继续从唐皇后身上汲取到那些关怀。皇后不甚懂朝政,倘若她要是懂了,后果如何呢……
“你说,这玉坠传了多少代,就有多少人受过折磨,”她的语气还是相当沉静,“我看不清她们的面目,听不见她们的声音。但我来到了这里。”
皇帝愈发恐惧,那不仅仅是生死的恐惧,他往后缩,身体却难以动弹:“胡说八道!她们都是自愿的!”
她分明是在指责他耗尽了她们的韶华!
“自愿的?”卫云舟挑眉,仿佛听见一个天大的笑话,“也罢,那就当她们是自愿的好了,可惜我现在不愿意了。如今没人可怜你了,陛下——”
声音陡然上扬,那如同丧钟一般的钟罄声音再度敲响,皇帝似乎要魂飞天外,他愣神,如是阴间神鬼。
“我来也不是为了让你加印,只不过给你看看罢了。”她冷笑。
皇帝呼吸急促起来,然后才渐渐平复,他大脑中过了很多很多事。
他突然眼前一亮,道:“你现在这么急,不就是赶这灾年?你那腹中胎儿,你是一点不顾——”
皇帝尚还清醒的时候打探过一二,这公主府中摆满了求子之物。看来是存心的,而后一些线报、迹象也表明如此。
“我能来这里,我腹中还能有什么胎儿吗?”但是卫云舟却无情打断。
皇帝张口结舌,意识到自己被骗之后,沉默片刻才道:“现在没有,不代表以后没有。你如今让那家伙做你驸马,以后难保不受他鱼肉——你当了皇帝又如何?”
还不是要给他生儿育女,一年半载后也当给他儿子——
“你眼睁睁地要将血脉污染,那没办法。”皇帝终于找到让自己信服的理由,他今夜终于得意起来。
卫云舟的脸上却扬起了一抹讥诮弧度。
她贴近,语调既轻柔又恶意:“可惜了,我同那驸马是虚凰假凤,她是个女人。”
霎时才完备起来的防线骤然又崩塌。
皇帝翕动了苍白的唇角,好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:“你,你,你们那是违背天下纲常——”
“对,违背天下纲常,”寒芒渗出皮肉血意,“可惜啊,从今天起,我便是纲常。”
皇帝不可置信地抬头,对上那双和唐禾极为相似的瞳孔。
意识逐渐涣散,钟罄声音不绝于耳,他轰然落下,却瞥见窗外似乎飘了什么东西下来。
“父皇,下雪了,”她声音还是轻柔,是对死者的垂怜,“在您下罪己诏的这一天,在我登上储君之